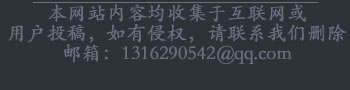首页 > 本地信息 / 正文
时间:2017年5月25日
地点:素象空间
嘉宾: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许知远青年学者
主持人: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五四”是一个长时段的文化事件
杨庆祥:对于每一位对中国未来保有美好信念的人来说,当我们回望历史,都不会忘记“五四”,不会忘记新文化运动。转眼,这个时间点距今已经快一百年了,每到“百年”都是一个值得回望和重点纪念的时刻。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回到当年那个历史现场,探讨关于“五四”、关于新文化运动之于我们今天还有哪些未解之题,以及“五四”跟我们当下的文化、当下的语境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对话关系。
杨念群:我对“五四”的理解,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时段里加以定位,它本身的意义其实不是一个政治事件,它更多是一个长时段的文化事件。
我自己理解,五四运动本身这个时段,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应该把它延得更长一些。我看大事年表里面已经把它从1915年一直延伸到1923年,我想还可能更往后延。“五四”这个时期孕育了一大批影响到我们当代学术、文化和意识的人才,他们可能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对整个世界,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看法,这是“五四”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五四”其实是一个现代史的开端和近代史的终点。我们应该更多从文化角度和它产生一大批民国精英的角度来理解。
当年任公先生(梁启超)写过一篇东西,叫《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认为中国经历了大致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器技之道”,就是我们被洋人打了之后感觉到疼,从军事的角度进行抵抗,洋务和引进的军事的东西基本上在这个阶段;后来进入制度阶段,大家觉得你有了器技之道、洋枪洋炮,最后为什么甲午战争还是打败了?进而形成戊戌变法的制度变革。最后第三阶段,任公先生实际认为就是“五四”阶段——所谓人的最终的觉醒。所有的制度和所有的奇迹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在伦理层面人本身没有觉醒的话,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将无法得到彻底改变。这是任公先生在那个时代理解的。
第二个看法,通过看这些信札和名人的一些交流,我觉得我们要对“五四”进行理解的话,大致要把它看成是几代人交替的过程。如果我们围绕《新青年》来看,像蔡元培先生,他是《新青年》的一个作者,但他本身又是一个标志,他当年是个革命者,是一个所谓的反政府、反清的人,后来转成了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同时又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奠基人。这几种角色从他的身上,实际是以“五四”这样一个节点来凸现出来的。它的第二批作者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海归”,在《新青年》的作者队伍里面就非常明显。像第三代后来出现了类似傅斯年这样的人。作为“五四”核心的这批文化圈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代际转换非常有意思。
第一代人政治的关怀非常强烈,像陈独秀,对现代国家的建立他有一套新的想法和展望。但是第二批作者进来之后,就改变了《新青年》整个的叙述结构,对文化的关注度明显提高,讨论的都是中国未来的文化问题。这批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个时代人的角色都是不断变化的。从那代人群体本身的身份认同和身份多元角色的一种转换中,我们看出新文化运动本身这样一种新的特质,而不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仅仅是“五四”运动一种单面的政治的那样一个含义在里面。
“五四”一代,同样面对全球化的过程
许知远:对我来说,“五四”是非常温暖又模糊、充满期待的旅程。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北大的时候,抱着对大学一种非常的向往,那是“五四”带给我的。我在高三的时候读了大量张中行的散文,他们描绘在沙滩红楼,那么一个非常自由散漫的北大,他们怎么样上课,怎么逃课。给我的印象,这样一个大学或者那样一个时代是某种自由灵魂的标志。我想每代人都是通过自我的生命体验、自我的困惑来接近历史的。那个时候也许是我幸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大有过一个小小的、规模不大的讨论风潮。陈平原老师当年编的很多书,比如《老北大的故事》,都是启迪我们心智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五四”对我最强烈的吸引是那种实验精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把历史人物变得非常地抽象化、模式化,傅斯年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名字,但如果我们回忆起来,他在1919年去办《新潮》杂志的时候,或许跟很多现在年轻人在宿舍里办一个自媒体公号是非常像的,几个好友他们产生了一种联结,他们想对时代发声,有可能这种情境是相似的。
关于“五四”,我另外一个追溯传统来自台北,殷海光。我当年去温州特意去找他的故居,“五四”精神那时候在我心中越来越明确了,殷海光和他的朋友们把某种“五四”的精神——对时代的批判精神、一种尝试精神、一种个人追求自由的精神带到台北,在那里奇怪地生存下来,辗转到后来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通过殷海光、通过发生变化之前的李敖等人转到我们身上。它是一个非常曲折的历程。
包括白先勇在《台北人》这篇小说里面讲了两个没落的北大的教授,一个在海外教书对着一群美国学生,讲美国学生永远无法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情结,另一个教授在台北,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无法疏解自己的感受,一心想去国外寻找一个教职。两个教授之间谈论“五四”现象,那一刻“五四”的失落、它曾经的荣光都特别地进入我的内心。
在过去一些年可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线索。我特别想知道,Google、Facebook在中国产生了很多衍生品,产生了微博、微信,然后产生了各种信息沟通和交流,这是全球化的影响,你可以追美剧、英剧,可以交流对特朗普当选你是什么感受,那“五四”一代的青年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五四”那一代面对的是另一次全球化的过程,一个由铁路、电报、电影、报纸、杂志构成的全球化过程。我们想到傅斯年也好,或者陈独秀办《新青年》也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印刷媒体革命的时代,那时印刷的质量越来越清楚,个人办杂志的可能性越来越强。倒推五十年,面对一个什么都要木板印刷,刻上去的一个高成本的年代,年轻人怎么样去组织自己的杂志来出版、来探讨?所以它后面是有一个全球背景,全球背景是否会影响他们的行为?据我所知,当年韩国在1919年他们追求独立的青年运动,潜移默化影响了“五四”,或者非常明确影响到了“五四”时候年轻人的感受。
那么我们再往前推,康梁他们是19世纪末的人,19世纪末中国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来自欧洲的危机,对他们的瓜分,对自己生存的焦虑。但是背后有没有别的东西?当时的全球思潮是怎么样的?他们那儿都是世纪末日。我们谈到世纪末日,就想起奥斯卡·王尔德在面对英国时的感受,左拉写《我控诉》时的感受,但是大家经常忘记了康梁是他们的同代人,他们的思想在那个时候产生某些新的传导。同时,康梁的思想又受到当时的李提摩太他们这些传教士报刊的影响。这些都是全球思潮,那中国的青年运动是否也是全球思潮的某一部分?就像我们此刻很多感受多大程度受到好莱坞文化的影响?多大程度受到西方正在变化的影响?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都会影响。我想那个时代全球的互相浸润程度,可能也远超我们此刻的想象。
谈“五四”的魅力,其实我们谈的是勇敢
许知远:我觉得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更宏观,同时也更个人化的理解来读解“五四”,理解他们内心的感受。我热爱“五四”那批人是因为他们是行动者,是他们思想的行动者——他们把某种思想转化成某种新的东西。我们现在反复谈五四的魅力,其实我们谈的是勇敢。“五四”人的思想,是他们要挣脱一个过去中国的八股文传统和各种各样思想传统的过程。你看他们的《新潮》杂志,看《新青年》杂志,这些文章没有什么可看的,就是一个常识的言说,按照绝对思想的意义。但这个意义无比巨大,一代人、两代人他们试图挣脱自己思维的窠臼,产生新的理念、新的感受力、新的探知世界的方式。那背后是什么?背后是勇敢,而勇敢可能正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最稀缺的东西,这个东西能够怎么影响我们的个体?
最后一个是共同体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对“五四”的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心怀憧憬,除去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觉得相对充满权力感的时代。过去一百年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而在康梁时代,梁启超一个25岁的年轻人,尽管在戊戌变法中他没那么重要,但是仍然很重要——他卷入到一个巨大的国家变革之中,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全国性变革力量的来源。到了“五四”时代,一个20多岁的胡适之可以成为全国青年的偶像,变成那个时代的周杰伦,这是某种知识分子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感在过去一百年里变得越来越萎缩。我觉得可能背后也有我们对权力的某种迷恋,对自己身份边缘化的耿耿于怀。
又回到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他们怎么写字,怎么交往,他们有一套类似的语言系统,来自一套知识精英的、来自过去士大夫传统的相互交流并自我确认的文化的交流方式。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发微信朋友圈,但确实找不到某种共同体的感觉。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去重新建立,建立知识分子的某种自我确认感——对信念的确认、对某种理念的确认、对知识本身尊严的确认,都变成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使命。
我想每一代人如果想重塑自我的话,都是跟历史发生关系。“文艺复兴”一代是要通过重新确认跟古罗马、古希腊的关系;康梁变法除了跟西方借鉴,也要确立跟尧舜禹的关系、跟宋代的关系、跟孟子的关系。到我们现在21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我们该怎么确认自己跟某种传统的关系?这都变成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崭新又趣味无穷的课题。
那我想当年“五四”那代人也是面临相似的课题,这种全球的困扰,自身传统的断裂,对自我意识的确认,都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杨庆祥:我最近正好在看霍曼写的《个人主义时代的共同体的建构》。他就提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基本上所谓的共同体和社会资本已经消耗掉了,没有办法建构起一个非常有效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沟通的共同体。
现在看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构不成共同体,在某种意义小圈子并不是共同体。共同体一定是有一个明确指向的使命感的东西,这一点恰恰是“五四”那一代人,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他们的构成非常复杂,有很老的,有很年轻的,他们普遍都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的使命感和历史的信念。这个东西其实是类似于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没有人有意识或者有自我意识召唤这样历史的天使,重新激活很僵化的或者非常体制化的东西,被均制化、异化的东西。
“五四”的存在有血肉感,不是教科书上冷冰冰的存在
杨庆祥:“五四”最重要的精神,其实是青年的精神。所谓“青年”的东西不是一个生理的问题,而是心理的问题、精神向度的问题。去年孙郁先生《鲁迅遗风录》出来的时候,我曾跟孙老师专门谈这个问题,我就说类似于《鲁迅遗风录》和对鲁迅这代人的精神打捞,最重要一点,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真实的、有血肉感的鲜活的“五四”存在,而不是教科书上冷冰冰的存在。这种方式才可以激活更年轻的一代进入到历史的现场。
孙郁: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后来改成《新青年》,其实他是有一个深意在里面。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年龄是最大的,30多岁;冰心是最小的,才19岁。
当时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最早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他们又推古希腊文化的介绍,认为人类初期、早期两希文明——希伯来和古希腊文明里面,有很多弥足珍贵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时候,人们认为年轻人也是这样,青年人的热情、青年人的想法、他们的热望在这个杂志里面都能表现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像冰心、胡适他们的文字还是比较有暖意的。鲁迅的文字就有一种沉重感,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自己的内心黑暗了,所以他说“要肩住黑暗的闸门,让青年往光明的地方去,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那就是让年轻人解放。
所以他后来搞未名社,就是跟“五四”的青年们在一起。他周围都是年轻人,那些青年翻译的东西他认为很有意思,像韦素园翻译果戈理,韦丛芜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李霁野翻译安德列夫,那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他们的翻译对后来中国的文学、文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他激活了年轻人身上的创造力。所以“五四精神是年轻的精神”我觉得是对的。
陈平原:去年我接“东方历史评论”的采访,做了一个问答,题目就是《20世纪是“五四”的时代》,我的观点,“五四”的意义包括酝酿、发生、纪念、重建、颠覆到最后上位。一百年来,学术界做了很多,我们也做了很多。“五四”是一个很幸运的时代,也是一个很幸运的运动——1919年发生,之后1920年起每年都纪念。1920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就在《晨报》上发表专栏文章,每年一期;再之后1939年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将之确定为青年节。“五四”的好处在于从来没被遗忘过,而“五四”遗憾的地方也正在于它每年都被纪念,就容易成为口号、让人家厌烦,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变得没有新鲜感。
我们现在感叹,那个成为口号的“五四”在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开始重新回到历史的情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重新理解1915年前后一直到一九二几年中间,那一代年轻人他们走过来的道路,也理解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的大量有趣、激动人心的事情和细节,从细节,而不是从口号入手来理解一个时代。
整理/本报记者吴菲
供图/小牧
(原标题:五四还有哪些未解之题?)
猜你喜欢
- 搜索
-
- 04-20好消息! 温州就业创业再出“一揽子”优惠奇乐听书网政策
- 04-17温州盲人大学生报考盲校教libido独占欲师受阻 视力是问题?
- 04-14人造人间奇凯达温州浙南科技城“千人计划”项目分享会诚邀您参加
- 04-11霸气!温州老爸50万复仇女神战术折刀买房车 停在校门口给女儿陪读
- 04-09格斗纹章修改器温州一季度高速公路完成投资24.47亿元!
- 04-07温州百永泽江里菜里路小学增加鹿城路新校区
- 04-07温州整蛊白领先生一房管局局长违规经商办企业 退休依然被处分
- 03-29精建精美!水枪版合金弹头温州下达2019年重大建设项目计划
- 03-29下月起 温州驾驶“无牌皮特老爹大战公鸡”超标电动车或被拘留
- 03-284月1名白雅美日起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温州办证在
- 标签列表
-
- 温州 (507)
- 浙江 (390)
- 历史 (272)
- 滴滴 (182)
- 顺风车 (166)
- 清朝 (76)
- 明朝 (72)
- 不完美妈妈 (71)
- 台风 (71)
- 文化 (70)
- 民警 (66)
- 杭州 (65)
- 高铁 (64)
- 网约车 (57)
- 房价 (56)
- 唐朝 (55)
- 乐清 (54)
- 房企 (54)
- 楼市 (53)
- 日本 (52)
- 中国历史 (51)
- 经济 (51)
- 政治 (50)
- 三国 (48)
- 城市 (43)
- 旅游 (42)
- 曹操 (41)
- 苍南 (41)
- 宁波 (41)
- 新疆 (40)
- 铁路 (39)
- 房地产 (37)
- 高考 (36)
- 交警 (36)
- 刘邦 (35)
- 失联 (35)
- 刘备 (34)
- 第二次世界大战 (34)
- 瑞安 (34)
- 上海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