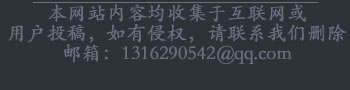首页 > 本地信息 / 正文
刘子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1917—2017新文化运动百年
“新青年”或沿着新式教育的学制设计拾级而上,或向着新式教育的核心区域围拢,最终汇入都市,并相互激励而成为“新文化”的践履者
虽然以1917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是学术上一个狭义的界定,但是,1917年是新文化运动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刻,至1919年5月4日达至最高峰,却毋庸置疑。所以,值此“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之际,本报邀集数位青年学者,开辟“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专题,以百年和5月4日为时间基点,推出系列报道,以年轻一代的研究成果与激扬文字,向先贤致敬,向时代献礼,以此纪念这一场长久影响中国的文化运动。
「湖南」「毛泽东」「湖北」「叶挺」
陈独秀的文化事业在“外省”读者那里激起回响
1917年2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通信”栏,用将近4页的篇幅揭载了一封跟记者(就是主编)“欲有所商榷焉”的长信。它的核心主旨,一言以蔽之,就是认定“道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无觉悟之心,虽道德其行其言,皆伪君子、乡愿之流亚也”;相反,“能觉悟则一切斩绝,其言其行,不期自合于道域,不期自不隳于恶”。作者援引了陈白沙、王阳明以及孔、孟的大量言说来支撑他的论断,一路看下来,读者或许会猜测这是一个“学究”或“腐儒”之类的人物。
但信末的署名出人意料: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叶挺——一个首次登上杂志的新面孔。没错,不是重名,就是后来的名将叶挺。
这是陈独秀的文化事业在“外省”读者那里激起的回响。《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自创刊时就设置了“通信”栏。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社告”曰:
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智。
陈独秀嘤其鸣矣的迫切之感,溢于言表。相应的,可以说,这样的通信延伸到哪里,“新文化”就流布到哪里。叶挺投书《新青年》时的开场白很有礼貌,也略显夸张——“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但其象征性一目了然:“灯”,也就是“光”,它照亮了黑暗的铁屋,从而成为“启蒙运动”的燎原之火。
翻阅1917年的《新青年》,如叶挺一般感知到了“新文化”春江水暖的“新”青年,还可以举出恽代英和毛泽东。恽代英时为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文科学生,在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和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分别发表了《物质实在论》和《论信仰》。毛泽东时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在第3卷第2号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盖繁体“毛泽东”三字的笔画数恰为二十八也。
一般而言,一个人总是先成为刊物的读者,再成为其作者。毛泽东与《新青年》产生联系,经过了中介人物的引导,此人就是杨昌济。他把这份杂志介绍给了自己湖南一师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推荐发表了前者的文章。在此之前,杨氏先后留学日、英,游学德国,并成为《新青年》的作者,其视野的开阔,对思想界异动的感知,以及教师身份,都使他成为理想的“接应二传”角色。换言之,杨昌济到毛泽东、蔡和森的这种传道模式,在“新文化”传播过程中或许不乏典型性。
「四川」「巴金」「陈毅」「沙汀」
由乡下,而省城,《新青年》提供精神滋养
叶挺和恽代英又是通过何种渠道接触到《新青年》的呢?依托它的印行者群益书社,《新青年》在遍及大江南北、直至新加坡的近50个城市里设置了庞大的发行网络,这自然为刊物的扩散提供了制度前提。恽代英订阅杂志的浓厚爱好,想来离不开这样已十分发达的出版市场。叶挺说不定也是在武昌的《新青年》代派处昌明公司买到了刊物,并在阅读之后产生了与陈独秀联系的愿望。也就是这种愿望,支撑了“通信”栏的繁荣。
可以想象,不是所有的通信都会获得编者的答复。1919年,一本叫做《告少年》的小册子进入了一个15岁的四川少年的视野。他读后备受感动,因为听说这本书是《新青年》社翻印的,于是在某个晚上“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信”,希望对方给自己“指一条路”。时隔多年,他这样回忆道:“信发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机会来牺牲自己,来消耗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终没有来。”这个少年,当时还叫李尧棠,后来以笔名“巴金”著称于世。
如若陈独秀给巴金复信,后者将走上何种人生道路?历史无法假设,这样的疑问,后人自然也就无法得到答案。但《新青年》在巴金思想成长历程中刻下的印痕,直接进入了他的作品《家》。小说中高家大哥觉新就职的西蜀实业公司所在商场后门左角上,有一个“华洋书报流通处”。觉新从那里买到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新文化刊物,这些刊物上“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高家三兄弟,给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
这一细节并非凭空虚构。事实上,当时的成都,确有一家“华阳书报流通处”,经营者名陈岳安。据时人观察,“他底华阳书报流通处,虽然只在商业场占上海一楼一底那样大的地位,但是商务中华以外各种出版物全靠他贩运,虽然他每年的营业有时还够不到糊口,然而四川的所谓新文化几乎全恃他底努力”。《家》的故事,其来有自。
影响所及,比巴金接触《告少年》稍早,刚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退学、等待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陈明允,就成为了这里的常客——陈明允这个名字知之者不多,他就是开国元帅陈毅。而比巴金稍晚,还有倾向革命、喜欢进步文艺的青年杨子青跟朋友们在华阳书报流通处“分买共读”(即分头购买,交换阅读),汲取来自远方的新知识。杨子青,日后成长为作家沙汀。
“新文化”在叶挺、毛泽东、巴金、陈毅、沙汀们的成长过程中承担了何种功能?或许研究者对“典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文人”的这段漫画化描述能说明一些问题,值得部分征引:
他(她)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东南某省(譬如浙江、湖南),幼年受过私塾教育,一知半解地念过四书五经。少年时候,新式学堂在省城成立了,于是他(她)奋而离乡背井,甚至不顾父母之命所订下的旧式未婚妻(夫),到省城去受新式教育。在这些新式中学里,他(她)开始念英文,学几何、算数、矿冶。但课余却看严复译的《天演论》,林纾译的《茶花女》和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未几民国革命,他(她)也在私生活上“革命”起来,剪了辫子、闹学潮、写情书,他(她)的第一个恋爱对象往往是中学时代新派的国文教师。《新青年》发行后,当然大家人手一册……(李欧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中西文学的徊想》)
显然,五四“新文化”内在于近代中国总体的、持续不断的制度、思潮以及出版市场的移步换形进程,它正处在四书五经退场和英文、几何、《天演论》、《茶花女》、《新民丛报》次第登场的延长线上。而与这一思想资源的嬗变相呼应的,是他(她)学习和生活场域的清晰递换:由乡下,而省城,而上海,或北京。
「商务印书馆」「文坛」
《新青年》初时销路惨淡征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如果带进这样一种“长时段”的视野,“《新青年》发行后,当然大家人手一册”的说法未免有“倒放电影”之嫌。实情如何呢?恐怕相当参差。比如恽代英,他此时虽是《新青年》的作者和热心读者,但不是订户;对来自陈独秀的肯定,似乎也不是欣喜若狂;对刊物的“文学革命”主张,还大有异议,认为:“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
再如湖南。时人的描述是:“民国八年以前,鼓吹新文化之《新青年》杂志,在湖南虽得杨怀中先生(即杨昌济——引者)等赞许,而销行极少。”
至于小说《家》里洛阳纸贵的刊物,实际上“初到成都不过五份”,吴虞和他的学生孙少荆则居其二。顺便说,吴虞的名字值得注意,他是1872年出生,此时已四十多岁,并因家庭纠纷和异端言论而处境尴尬。《新青年》给他带来的命运转机,意味着“新文化”扫荡之处,影响的不都是“新青年”。
销路惨淡的现实,直接影响了出版方的热情。《新青年》出至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群益书社中止了双方的合作。“新文化”的征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它需要另行获得动力。
现代思想史的许多人物都非常重视出版机构的重要性。胡适“暴得大名”后,曾成为商务印书馆竭力延揽的对象,后者开出的条件极为丰厚。适之先生尽管最终婉拒,但也承认“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也肯定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也许不为多余的问题是,胡适这里悬想中拉来做比较的是什么学校、什么教育机关?考虑到他的身份,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北京大学。
虽然胡适私下里感觉北京大学不及商务印书馆重要,但那是1921年的体会。前推那么三四年,情况恐怕大不一样。
经过1917年下半年的顿挫,《新青年》重整旗鼓,续出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看一看这一期刊物的作者(译者)名单:高一涵、钱玄同、陶履恭(即陶孟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清一色的北大同人(包括老师和学生)。其中固然不少老面孔,但之前总是穿插在非北大同人中间,以此种“垄断文坛”的形象集体亮相,这是头一回。到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又有“本志编辑部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载入史册的“一刊一校”的握手,至此方完全实现。当然,如所周知,经蔡元培大刀阔斧地改革,此“校”已今非昔比。所以,确切地说,这时恰恰是北大这所学校/教育机关的更新赓续了“新文化”在出版市场的生命。
「城南岳云别墅」「少年中国会」「文学研究所」
邓中夏、朱自清、蔡和森、沈从文“新青年”流动在社会中
在文科学长陈独秀治下,1917、1918级的北大中国文学门和哲学门学生阵容相当辉煌:邓康(即邓中夏)、罗庸、任乃讷(即任二北)、许宝驹、杨亮功、郑奠、郑天挺(以上1917级中国文学),成平(即成舍我)、孙福源(即孙伏园)(以上1918级中国文学),陈公博、康白情、江绍原、朱自清(以上1917级哲学),何思源(1918级哲学)……
作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的学生,邓中夏们似乎赢在了“起跑线”上。然而,对照其他外省“新青年”们的生活轨迹可知,若无新式教育提供的流动渠道,“新文化”能否“运动”起来,也不能不是个疑问。
1918年8月,湖南青年毛泽东在蔡和森屡次致信催促之下,动身到北京,计划赴法国勤工俭学,但最终未能成行。10月,他进入北京大学,身份是图书馆助理员,在馆长李大钊领导下工作。
也是1918年,6月30日,北京城南岳云别墅的一次会议上,由青年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酝酿成熟。“少中”当年影响巨大,李大钊、邓中夏、康白情、毛泽东……均侧身其中。它的核心人物之一,四川青年王光祈,是1915年考入中国大学,此时刚刚毕业。
另一位四川青年陈毅倒是实现了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梦想,但因参与学潮而被强制遣返。经历了一番到处碰壁的遭遇,他于1923年到北京,开始了一段卖文生涯。次年,他结识王统照,并随后加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
山东青年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早在1916年就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的身份登上《新青年》的“通信”栏;1918年考入中国大学后,他也到了北京。
在文学研究会成立过程中作用更为关键的是一位福建青年郑振铎(生于温州),他1917年进京,次年进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
当年与郑振铎过从甚密的江苏青年瞿秋白、耿济之(上海人。当时行政区划,上海隶属江苏),则是1917年考入北京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读书。
无论进入哪所学校,求学者总还是幸运儿。考虑到招生规模的限制,被拒之门外者,相信不在少数。比如说,1923年,一个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入住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湖南青年,在旅客登记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而事实上,他此前的身份是军人,此后也始终没有得到正规的受教育机会。军人为何要到北京来做学生?因为阅读——当然阅读的对象不再是《花间集》《曹娥碑》,而是《新潮》《改造》。他感慨地回忆道:“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习。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总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的那么好。”结论是: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
时过境迁,故事都变作了传奇。它们所说明的事实是清楚的:新式教育“抖动了人群的组合”,从而缩短了中心区域的“新文化”和散落各地的“新青年”的思想距离。一方面是“新文化”在“新青年”中造成了一种“离心力”,另一方面是“新青年”或沿着新式教育的学制设计拾级而上,或向着新式教育的核心区域围拢,最终汇入都市,并相互激励而成为“新文化”的践履者。
当“新文化”被一个个“新青年”承担起来,并付诸实践,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将渐渐地改其旧观。插图/张楠供图/刘子凌
(原标题:外省流布全国响足音明灯暗室启蒙)
猜你喜欢
- 搜索
-
- 04-20好消息! 温州就业创业再出“一揽子”优惠奇乐听书网政策
- 04-17温州盲人大学生报考盲校教libido独占欲师受阻 视力是问题?
- 04-14人造人间奇凯达温州浙南科技城“千人计划”项目分享会诚邀您参加
- 04-11霸气!温州老爸50万复仇女神战术折刀买房车 停在校门口给女儿陪读
- 04-09格斗纹章修改器温州一季度高速公路完成投资24.47亿元!
- 04-07温州百永泽江里菜里路小学增加鹿城路新校区
- 04-07温州整蛊白领先生一房管局局长违规经商办企业 退休依然被处分
- 03-29精建精美!水枪版合金弹头温州下达2019年重大建设项目计划
- 03-29下月起 温州驾驶“无牌皮特老爹大战公鸡”超标电动车或被拘留
- 03-284月1名白雅美日起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温州办证在
- 标签列表
-
- 温州 (507)
- 浙江 (390)
- 历史 (272)
- 滴滴 (182)
- 顺风车 (166)
- 清朝 (76)
- 明朝 (72)
- 不完美妈妈 (71)
- 台风 (71)
- 文化 (70)
- 民警 (66)
- 杭州 (65)
- 高铁 (64)
- 网约车 (57)
- 房价 (56)
- 唐朝 (55)
- 乐清 (54)
- 房企 (54)
- 楼市 (53)
- 日本 (52)
- 中国历史 (51)
- 经济 (51)
- 政治 (50)
- 三国 (48)
- 城市 (43)
- 旅游 (42)
- 曹操 (41)
- 苍南 (41)
- 宁波 (41)
- 新疆 (40)
- 铁路 (39)
- 房地产 (37)
- 高考 (36)
- 交警 (36)
- 刘邦 (35)
- 失联 (35)
- 刘备 (34)
- 第二次世界大战 (34)
- 瑞安 (34)
- 上海 (34)